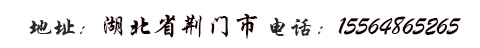北京小菜儿,芥末墩儿吃过没北京范儿
|
芥末墩儿是北京的家常菜。 应该也是北京独有的一种吃食。 其实就是芥末白菜的升级版。 把白菜围成一个小圆墩儿,上面浇上芥末膏。 很爽口的。 尤其是在春节,北京人家家都会有这道菜。 给春节大鱼大肉的油腻里,添一道清爽的风景。 北京人吃饭的“穷讲究”就在这道菜里很充分的表现出来。 明明就是芥末膏拌白菜,但是非得把它做出一个造型。 显得那么高端大气上档次。 其实原材料不过就是大白菜而已。 而且,您不把它卷成墩儿,就直接切成片用芥末腌也可以。 但是,北京人就还是要把它卷成墩儿。 据说这是一道宫廷菜。 呵呵,北京很多东西都要和宫廷扯上关系。 那没有办法,谁让紫禁城就在北京呢。 就连肉墩墩的“门钉肉饼”都要说成跟慈禧有关系的。 是这么说的,慈禧的厨师做出来独创肉饼给老佛爷尝。 然后慈禧问:“这叫什么呀?” 厨师没有想名字,看到宫门上的门钉,急中生智说:“就叫门钉肉饼” 其实这些都是民间传说,是老百姓的臆想。 您细究就没有道理。 慈禧怎么可能在能看到大门的地方吃肉饼呢? 您以为她也是去故宫旅游的哪。 所以这芥末墩儿是不是宫廷菜咱们就不深究了。 姑且信之,如何。 反正,北京的老百姓希望它是宫廷菜。 也希望它是过去皇上喜欢的。 最主要的是这样说起来,自己吃着也提气不是。 北京老百姓对大白菜的喜爱,或者说是依赖。 是有历史渊源的。 早年间,北京的冬天什么蔬菜都没有。 尤其是困难时期。 老百姓过冬,唯一能吃到的蔬菜就是大白菜和萝卜。 萝卜有一阵还限购,能保障的就剩了这大白菜。 我奶奶那一辈人,就是正好生活在这物质匮乏的年代。 也就是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的北京冬天比现在冷。 还能看到鹅毛大雪。 还能堆雪人儿。 哈哈,关心的东西不一样哈。 因为我看到过我爸爸小时候堆雪人的照片。 雪看起来有一巴掌厚。 现在的北京真的看不到这么大的雪了。 每到入冬,大白菜收获的季节。 每一个胡同的街道就会组织农村运大白菜的大车。 往城里运送大白菜。 那时候就叫冬储大白菜。 我爸跟我说过,他小时候,家里一定要有大白菜的储备。 如果没有,那就是恐慌。 通常拉白菜的大货车都来的很早。 所以整个胡同里的居民就会在太阳没有出来的时候, 就去排队。 当大货车露头的时候,看胡同里的队伍早已经排的很长了。 我爸说,那时候的冬天,只有很少的商店能有*瓜和西红柿卖。 而且,很贵不说,还要凭票。 他们小时候,能在冬天手里攥着一条*瓜在胡同里边吃边走。 不亚于现在手里抓着一只澳洲大龙虾。 直到几年前的冬天,我奶奶还是要冬储大白菜。 每一年我爸都要劝她。 不用啦,现在的白菜没有那么紧缺了。 菜市场里有的是。 而且,现在住楼房,存大白菜也没地儿放啊。 不方便。 我奶奶固执己见。 她宁可把白菜放到楼前面的绿化地里。 然后用塑料布盖上。 也要有冬储大白菜。 其实,每一个冬天,我奶奶储存的大白菜都有很多干瘪了, 烂掉了,最后开春的时候都扔掉了。 我奶奶在心疼之余,还是要在冬天储存大白菜。 她说,习惯啦,冬天要是没有大白菜就觉得缺点什么。 家有余粮心里不慌啊。 您别说,还真的有那种开着电动板车来小区里专门给这些老人送白菜的。 我看到小区里的很多爷爷奶奶都在冬储大白菜。 他们还自发的组织分地盘。 这一块儿是谁家放,那一块儿是谁家放。 看起来井井有条。 我爸也就不管了,这可能是老人怀旧的一种方式吧。 芥末墩儿这道菜和北京的炸酱面类似。 每家和每家的做法从大面上看都差不多。 但是细节都是各有特点。 比如,在处理大白菜的时候。 有的家里是用水直接焯水。 而有的家里是用开水浇白菜。 我奶奶说,她年轻的时候,也是用开水浇。 就是把白菜的叶子都扒下来, 一片片的排好。 然后用开水浇透叶子。 让叶子断生。 这样做出来的芥末墩比较脆。 后来上了岁数,牙口不好了,就开始用开水焯了。 反正万变不离其宗。 目的都是把生的大白菜断生。 然后把芥末膏涂在大白菜的表面。 再放上白糖和白醋。 放到冰箱里冷藏一晚上。 味道也都腌进去了。 第二天吃的时候,挑出三四片大白菜的叶子。 一个压一个的摆好。 然后用手卷起来。 卷的时候稍微的用些力气。 把白菜卷成一个厚厚的卷。 放到案子上,用刀切成三四厘米长的小段儿。 竖着摆在盘子里。 然后把盆里头天晚上腌白菜的汁浇到这个白菜墩上。 就大功告成啦。 这芥末膏我要特别的说明一下下。 这不是我们通常说的日本芥末膏。 而是北京本地的土产。 以前是怎么做的我不知道。 我看我奶奶做的时候,是从超市买的芥末粉。 这调芥末膏也是有学问的。 先用开水把芥末粉冲开。 搅拌均匀。 稍微的晾一下。 然后要放到冷水里镇一下。 这就是很关键的一步。 有科学道理的哦。 芥末这种东西就是要冷热变换的刺激一下。 才能把味道激发出来。 不这么操作,就弄不出刺激的芥末味。 这芥末膏也是北京人习惯吃的食品。 类似麻酱,类似蒜汁儿。 您可以在很多老包子店看到这个芥末膏。 很多外地同事都很奇怪的问过我。 这是要蘸着包子吃的吗? 你们北京人好奇怪,吃包子为什么要蘸芥末。 您问我,我问谁去呀。 我们这儿都是这么辈辈儿传的吃法。 怎么能找到原因呢。 不知不觉奶奶离开我都已经两年了。 我家的芥末墩也同时失传了。 我爸和我妈都试着做过几次。 每次和每次都味道不一样的。 而每一次都没有找到奶奶做的味道。 我很怀念我奶奶做的芥末墩儿。 我也很想我的奶奶。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ozhoulongxiaa.com/azlxyz/12381.html
- 上一篇文章: 十三香油焖的蒜泥的清蒸的,小龙虾怎
- 下一篇文章: 前一天还在澳洲海里游的龙虾次日就能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