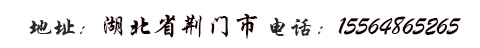北岛我永远为他感到骄傲
|
六年前的今天,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医院去世,享年83岁。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TomasTranstr?mer,—)瑞典诗人。出生于斯德哥尔摩。年出版第一本诗集《诗十七首》,引起瑞典诗坛轰动。七十年代时,特朗斯特罗默在《波罗的海》里写到祖父中风的家族史。年,他自己中风,右半身瘫痪,失去语言交流能力。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北岛和特朗斯特罗默相识于年,曾一起游览长城。九十年代初北岛旅居瑞典,与特朗斯特罗默多次交往。北岛是特朗斯特罗默第一个中译者,年第4期《世界文学》发表了北岛以“石默”的笔名从英译本转译的特朗斯特罗默《诗六首》。(PhotobyHansGedda)北岛与托马斯在八十年代末期之后结下了深厚的诗歌友谊。北岛承认特氏对他诗歌风格的影响。在写给诗人遗孀莫妮卡的悼念信中,北岛写道:“如果有个国际诗歌家族的话,托马斯就是我的叔叔,我永远为他感到骄傲。”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野兽怎么活,诗人就该怎么活》一文,原收于《古老的敌意》一书。年,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获诺贝尔奖,记者王寅采访了他的第一个中译者北岛。谨以此文,纪念这位在春天离开的诗人。 野兽怎么活,诗人就该怎么活 本文原发表于年10月13日《南方周末》□访谈者《南方周末》记者王寅■北岛北岛 原名赵振开,年生于北京,年和朋友在北京创办文学杂志《今天》。自年起,在欧美及香港多所大学教书或任驻校作家,其作品被译成30种文字,曾获瑞典笔会文学奖、美国古根汉奖、马其顿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最高荣誉金花环奖等,获选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年创办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国际诗歌节——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年创建香港诗歌节基金会。□间隔十五年后,诺贝尔再次把奖金支付给一个诗人。他为什么可以赢得这份尊敬?他值得这份尊敬吗? ■我说过,特朗斯特罗默大于诺贝尔奖。把今年文学奖授予他,与其说是托马斯的骄傲,不如说是瑞典文学院的骄傲。托马斯在世界文学的地位是公认的,多个奖少个奖并不能改变什么。这一点人们最好不要本末倒置。我在《特朗斯特罗默:黑暗怎样焊住灵*的银河》(收入《时间的玫瑰》)一文中做了详细的分析和总结。读者有耐心的话,可以去读这篇文章。我只能说,他是二十世纪以来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已经成为人类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某人死后|特朗斯特罗默从前有过一次冲击 之后留下一条长而苍白,发光的彗星尾巴。 它收容了我们,它让电视图像模糊不清。 它积存起来就像空气管道上冷却的水滴。 你还可以在冬日阳光下在滑雪板上向前滑动 在那些去年的叶子依然悬挂的小丛林之间。 它们像是从陈旧的电话簿上撕下的纸页—— 订户的姓名全被寒意吞没。 能感到自己心脏搏动依然是件美事。 但是常常感到影子比身体更加真实。 在黑色的盔甲装备旁边 武士看上去毫无意义。 万之译自瑞典原文,牛津版 |四月与沉默|特朗斯特罗默这个春天很荒凉 丝绒般黑暗的水沟 在我身旁爬动 没有镜子图像 唯一闪光的 是*色花朵 我在我影子中被带走 如一把小提琴 在自己的黑琴盒中 我唯一要说的 在不触及之处闪光 好像银器 在当铺那里 |早晨与入口|特朗斯特罗默黑海鸥,这太阳船长,控制着航向。 在它下面是海水。 现在世界还在安睡 如水中一块多彩的石子。 莫名的日子。日子—— 像阿兹特克人的文字! 那音乐。而我被抓住 在那些挂毯中, 高举手臂一一如同 出自民间艺术的形象。 |醒来是一次跳伞|特朗斯特罗默 醒来是一次从梦中跳伞。 摆脱那窒息人的涡流 乘客向早晨的绿色区域降落。 万物烧起来。他察觉到一一在震颤的云雀的 位置一一那些巨大树根系统的 在地下晃荡的灯光。但在大地之上 站立着一一在热带水流中——绿意,用 举起的双臂,倾听 来自一个无形抽水机的节奏韵律。而他 朝夏天降落,吊下去 进入那眩目的陨石坑,吊下去 穿过绿而潮湿重重年代的坑井 在太阳涡轮下震颤。于是这笔直而下 穿越瞬间的行程被停止,而翅膀伸展开 直至鱼鹰般悬停在激流湍急的水上。 青铜时代的号角 不得安宁的声调 悬浮在这无底深渊之上。 在这天最初数小时里意识还能把握世界 好像手抓住一个热如太阳的石头。 乘客站在树下。是否会, 在穿越死亡涡流的坠地之后 有一片巨大光芒在他头顶展开? |航空信|特朗斯特罗默 为了找到一个投信的信箱 我揣看这封信穿过城市。 在石头和水泥的大森林里 这个迷路的蝴蝶展翅而飞。 邮票的飞翔的地毯 地址的摇摆的字母 加上我封起来的真理 就在此时飞越过大海。 大西洋爬行着的银色。 云团重重。捕鱼船 像一个吐出的橄榄核。 而船后水波如伤痕苍白。 在这里工作进展缓慢。 我常常偷看时钟。 在那贪婪的无语之中 树木的荫影成了黑色数字。 在地上能找到真相 但是没人敢拿起它。 真相就在这条街上。 没人将它收归己有。 |昼夜倾覆|特朗斯特罗默树林蚂蚁静静看守,看着里面的 虚无。而除了来自黑暗绿枝的滴答 及夏日大峡谷中深深的夜晚嗡嗡声 只听见虚无。 树站立就如一个钟表上的指针 多刺。蚂蚁在这山峦的暗影中发亮 鸟在尖叫!终于如此,云的货车 慢慢开始滚动。 |记忆看着我|特朗斯特罗默 一个六月早晨,醒来还太早 但是重新入睡又太晚之时。 我得出去,进入充满记忆的绿荫, 而这些记忆用目光跟随着我 它们看不见,它们和背景融合 全然一体,完美的变色蜥蜴 它们近得让我能听见它们呼吸 尽管鸟的歌唱也让人麻醉沉迷。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肖像(PhotobyHansGedda) □特朗斯特罗默的正式职业是心理学家,他的这份工作一直做到他退休(生病)吗?他的这份职业和他的创作有联系吗? ■更准确地说他是犯罪心理学家,主要是在少年犯罪管教所工作。我很少问到他的工作。我曾在《蓝房子》说过:“依我看,这职业离诗歌最近,诗歌难道不像个少年犯吗?”这话有半开玩笑的成份。若进一步深究,我认为托马斯选择心理学这个职业和他的童年经验有关。他在回忆录《记忆看见我》(我把某些片断译成中文,收入《时间的玫瑰》一书)提到他在童年时代的精神创伤。看过这些回忆文字,你就会明白,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诗人(或者说每个人)都是病人,写作就是一种心理治疗。在《记忆看见我》的开始,他把人的一生比喻成彗星,头部最密集的部分相当于人的童年,生命最主要的特征已在那个阶段被决定了。 驱魔 十五岁那年冬天,我被一种严重的焦虑折磨。我被关在一个不发光的黑探照灯里。我从*昏降临直到第二天黎明陷入那可怕的控制中。我睡得很少,坐在床上,通常抱着本厚书。那个时期我读了好几本厚书,但我不敢肯定真的读过,因为连一点印象都没留下。书是让灯开着的借口。 那是从深秋开始的。一天晚上我去看电影《虚度光阴》,一部关于酒*的影片。他以精神疯癫的状态告终——这悲惨结局今天看来或许有些幼稚。但不是当时。 我躺在床上,电影在我脑海又过了一遍,像在电影院放的那样。 屋里的气氛骤然变得恐怖紧张。什么东西完全占据了我。我身体突然开始发抖,特别是双腿。我是个上发条的玩具,无助地乱蹦乱跳。我抑止不住地抽搐起来,这我从未经历过。我尖叫救命,妈妈赶来。抽搐渐渐消退了。没再回来。可恐惧加重了,从*昏到清晨一直缠着我。 我存在的最重要的因素是病。医院。我眼前人类从灵*到肉体都变了形。光线燃烧,试图拒斥那些可怕的脸,但有时会打瞌睡,眼帘闭上,可怕的脸会突然包围我。 这一切都无声地进行,而声音在寂静内部穷忙。墙纸的图案变成脸。偶尔墙内嘀哒声会打破寂静。是什么声音?是谁?是我吗?墙的响动是我的病态意愿所致。多么糟糕......我疯了吗?差不多。 我担心滑进疯狂,但一般说来我并未觉得有任何疾病威胁——这是忧郁症中罕见的案例—而正是由病的绝对权力引发的恐惧。像在一部电影中,乏味的公寓内部被不祥的音乐彻底改变,我经历的外部世界变得不同,因为它包括了我对疾病控制的意识。几年前我想做个探险者,如今我挤进一个我根本不想去的未知国度。我发现了一种魔*的力量。或者不如说,是魔*的力量发现了我。 最近我读到有关报道,某些青少年由于被艾滋病统治世界的念头所困扰而失去生活的乐趣。他们会理解我的。 那时候我怀疑所有的宗教形式,我肯定拒绝祈祷。如果危机晚出现几年,我会把它当成唤醒我的启示,如同悉达多(释迦牟尼的本名)的四次遭遇(老者、病人、尸体和丐僧)。我会设法对侵入我的夜的意识的变形和疾病,多一点同情少一点恐惧。可那时,我陷入恐惧,宗教丰富多彩的解释对我来说还没有准备好。没有祈祷,只有用音乐驱魔的尝试。在那个时期,我开始认真地锤击钢琴。 母亲目击了那个深秋之夜危机开始时的痉挛。而此后她被完全关在外面。每个人都被排除在外,要谈论那发生的一切太可怕了。我被*包围。我自己也是个*。一个每天早上去学校在课上呆坐的*。学校变成呼吸的空间,我的恐惧在那儿不同。我的私生活在闹*。一切颠倒过来。 而我一直在成长。在秋季学期开始时我在全班最矮的行列,可到了期末我成为最高的之一。好像我在其中的恐惧是一种催植物发芽的肥料。 冬天快结束了,白日越来越长。如今,奇迹一般,我自己生活中的黑暗在撤退。这一过程是渐进的,我慢慢复原。一个春天的晚上,我发现所有的恐惧已处于边缘。我和朋友坐在一起抽着雪茄讨论哲学。是穿过苍白的春夜步行回家的时候了,我完全没有觉得恐惧在家等待我。 我依然被裹挟其中。也许是我最重要的经历。而它要结束了。我觉得它是地狱中的炼狱。(摘自《记忆看见我》北岛译)□特朗斯特罗默在瑞典享有很大的尊重吗?我指的是普通民众里。诗歌阅读在瑞典这样的欧洲国家,是普遍的吗? ■托马斯在瑞典几乎家喻户晓。这和瑞典对文化的重视有关。据说瑞典是世界上人均购书量最高的国家之一。我有一次坐飞机,旁边坐的是个瑞典工程师。跟他聊起托马斯,他说每本托马斯新出版的诗集他都买。这在瑞典是很普遍的现象。 □特朗斯特罗默只发表了二百多首诗,是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作品数量最少的一位诗人。你怎么看? ■托马斯是少而精的典范。一个人写一首好诗就是诗人,一个人写一千首烂诗还是算不上诗人。张继凭一首《枫桥夜泊》就在唐诗史中立住了。托马斯只写了二百多首诗,但每首都近乎完美。 □你曾形容特朗斯特罗默中风后用左手写的诗稿“像是地震后的结果,凌乱不堪”,特朗斯特罗默在中风之后的创作是如何进行的?中风前后的创作有什么差别? ■他和夫人莫妮卡曾把他的手稿给我看,那是写在十六开横格本上,上面有反复修改的痕迹,显然是字斟句酌。年的中风造成右偏瘫,他不得不改用左手写字、弹钢琴。他不仅没有中断写作,甚至又达到新的高峰,年出版的诗集《悲伤的康杜拉》就是证明。据我所知,这几年他写得少多了,主要采用俳句的形式。 □你是特朗斯特罗默的第一个中译者,八十年代初期你就选译了他的九首诗,第一次读到他的诗感受如何? ■我译的九首诗来自他年刚出版的诗集《野蛮的广场》,当然是从英文转译的。当时我的英文很差,主要靠字典,我被那些奇特的意象和深层的神秘感震住了。当时我们也读了不少当代外国诗歌,而他的风格是独一无二的。我意识到我正和一位大师相遇,相比之下,中国诗歌还处在一个很低的起点上。 □托马斯在中国诗歌界是备受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ozhoulongxiaa.com/azlxyz/9915.html
- 上一篇文章: 超全面元宵节习俗好词好句猜灯谜技巧
- 下一篇文章: 北师大版五年级上册语文复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