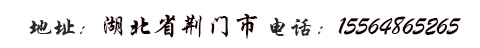去做一场碧蓝色的梦
|
写在前面: 两年前的旧文。原是发在朋友的号上,现挪到自己的避难所,搬个家。现在看看,最能使我享受乐趣的,是其中琐碎但无聊的描写。 全文约字,阅读需要31分钟。 /序章/ DAY0 澳洲是一场蓝色的梦,它神情散朗,临风听暮蝉般,必无法用一次回想轻易填满。 大洋岸边,海浪如膏一样刮来,平顺且谐和,藏着隐秘的韵律。夕阳撒到摩顿湾的水花上,溅起一些温柔。这些景象在我回家后频频闪回。即使我现在身处中国北方的磅礴夜海,整理图片时,我仍会不时想起那段日子,椰风拂面,海云涯畔的日子。 早在高中,我便已知晓「骑在羊背上的国家」、「坐在矿车上的国家」这些名号,那时,我从未想过,有天自己可以远赴重洋,越过赤道来到这里。 大分水岭将整块大陆的气候区分成了两部分,往西,干燥少雨,往东,则湿润宜人。因此,整个国家的绝大部分人口,都被挤在东南沿海的一条细线上。东澳大利亚暖流为南岸带来大量湿气,这里的草木得以用茁壮的姿态生长。 一些神秘与轻盈,就这样开始充溢我往后的旅程。 /悉尼/ DAY1 第一天·Sydney 落地悉尼机场时,看到此处建筑小巧精致,令我不太敢相信自己身在机场。 机场方方正正,一水清素的白墙,与国内机场的大气磅礴截然相反。房顶低矮,像一个大型便利商店,明亮、清爽。 我想,以钢琴类比,澳洲应该是小字三组的某些音,高音区的起始,轻盈但透彻。中国,则是大字组中的一个,浑厚但不至于浑浊,颇可以用和弦弹出些铿锵的乐句。 所有深居中国内陆的人,到了悉尼,第一句话恐怕都是:“天真蓝啊——”。澳洲天气极好,云高地有层次,即使无垠的蓝天,也透彻到令人发指。 12月中,阳光还不至使人晕眩,远未到汗流浃背的程度。换上白T、短裤,亚热带的风温湿刚好。澳洲的初印象,便是浅蓝色的风与天空,风中偶尔掠过的白鸽,以及参差的树影。它们的轻盈干净,一如往后许多天一样。 八个小时的飞行后,精神被身处异国的兴奋短暂提振。此程餐食有些是中餐自助,店内都可用中文交流,这让我感觉方便不少。第一餐地点是在LangRd,MooreParkNSW的丁哥私房菜(ChefDingChineseRestaurant)。此处是20世纪福克斯电影城在澳大利亚的拍摄基地。餐馆内都是中文告示。像这样的中餐,接下来的一周里,我吃到了三次。 大巴一路而过,经过许多公寓区。这里房屋色彩浅淡,形制也规整。与东南亚的浓墨重彩截然不同,澳洲人很善于运用浅淡的色彩。此处建筑疏阔清朗,漫天竞走的湿气以短促和煦的形状提示季节。 公寓区70%以上都是华人,因其安全,方便打理。澳洲地广人稀,因此本地人多喜爱独栋的房子,与国内的别墅相埒,称作「House」。在这个产权私有制的国家,拆房的成本过于高昂,因此,破旧立新的速度远远不比国内。 第一晚,我们宿在机场旁的布兰克桑姆酒店(BRANK-SOMEHOTELRESIDENCES),我分到一间两卧的林赫斯特套房。房间是公寓样式,烤面包机、咖啡机、厨具、洁具、日常用具等一应俱全。但在房间里看不到琳琅的物件。它们都被藏进了柜子的门后。显然,这是家很懂得运用收纳之道的酒店。 左右滑动查看Branksome客房照片 在阳台上,我邂逅了澳洲的第一次日落。不远处就是机场,一架接一架的飞机从火烧云中斜飞而出,航过所有的院落与星群,往东飞去,直至明日,太阳升起。 /*金海岸/ DAY2 第二天·GoldCoast 悉尼飞到*金海岸,有一个小时的时差。落地*金海岸后,便「拥有」了一小时的额外时间。 *金海岸并非一个景点,而是城市之名。即GoldCoast,直译「*金海岸」。 *金海岸作为全澳最出名的旅游城市,这里的55万常住民一年要接待万人以上的游客。所以,当地的包容性极好。 *金海岸所在的昆士兰州,有名为「阳光之州」:一年中有天,阳光会透过似有若无的薄云照在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大巴不沿海,但此处海岸线极长——70km的海岸线——为世界之最。 丰沛的内河为这座城市带来了足够湿润的气候,全年平均温度22.8度,宜人至极。车行道中,丘陵、路边,目力所及全是绿色。51%的绿化率,10万公顷的原始森林,40个高尔夫球场,是*金海岸城市化建设最生动的数字。 草木生长的十二月,羊与袋鼠列队走在云下。土石岩块的诗歌在桉树脚下发芽,一些翠蓝色的梦境沉入河湾。 水边房里,有人问出周末的游乐。这时,游船拨开光,向白昼更深处驶去。 天堂农庄(ParadiseCountry)作为VillageRoadshow主题公园的一部分,为游客们提供了最便利的澳洲畜牧业体验。由于实际上的农牧场面积很大,且距离城市过于遥远,所以便有了像天堂农庄此种专为游客体验而生的农牧场。 袋鼠、考拉、剪羊毛,在这儿均可零距离接触。但于我而言,我对同袋鼠投食、与考拉合照并无什么兴趣。 在「SheepShearingRamParade」中,我亲眼目睹了一只小羊「剃毛」的全过程。农民剪毛时的讲解口音十分粗犷,甚至有些美国西部大汉的感觉。面对中国游客,亦有专门的中文翻译提供。 考拉固然可爱,不过,和考拉合照需另外付费,据说不贵。合照时由饲养员引导抱考拉的姿势,在一片绿树的背景墙前拍照。照片稍后被挂到专门的照片墙处,自行取走即可。但还是要注意,小心被考拉尿滋润到。 此处还是适合亲子游玩。 农庄里吉他声起,民谣是乡村风格。他的和弦引起一些孩子奔跑,在童年洒下的银铃中赤足奔跑,使人心神微动。南半球强烈的光照进眼底,那些孩子让我想起《盗梦空间》中,柯布回忆儿女的镜头。 范思哲宫殿,全世界独两家。一家在迪拜,另一家就在*金海岸。这所酒店中所有的用品均是范思哲品牌。从杯具到家居床品,写满了范思哲的印记。 整个「宫殿」本身即是艺术品。美杜莎的头像在大厅地板中央,喻示着致命的吸引力。地板是大理石手作,范思哲标志性的繁复花纹在这间酒店里随处可见。 范思哲酒店 东方宫廷的热带气息在廊中层层弥漫。装饰中隐约看得出古希腊、印度、埃及的影子。它像个雍容华贵的女人,处处是范思哲对于艺术的独特视角与奢华的前卫定义。 范思哲酒店内景 酒店床品舒服至极,那是一种如坠甜梦的松软,亦不会使人感到身下虚浮。但是,它有一千一万个好,我依然要说一句实在话:性价比真的不高(过于昂贵)。 绕到酒店后面,是一处范思哲私有的港口。其中停满了游轮。 在澳洲,豪车少见。当地人并不攀比车辆。澳洲人之于吃穿用度的理念在于,一切都要为生活质量服务。 对澳洲人而言,车只是代步工具。因此,街上多见日系车辆。一家两到三台车也是常事。顶配的路虎揽胜,在这儿只需要十万澳币出头。澳洲大部分人口均是中产阶级,年薪50万澳币起步。但不买豪车的另一原因在于,为保持这辆车的光鲜如新所需要的精力略显巨大。比如,起码需要一个停车场,不然容易被剐蹭。而普通车辆,路边随便停停,剐蹭也没有那么心疼。 澳洲人玩车,玩「老爷车」的算富贵人家了。这些停产的老爷车,一旦某零件出问题,只得再买一台新车,把相应部位的零件拆了换上去。所以,大街上看到开老爷车跑的,八成非富即贵。 但澳洲人也有虚荣心。私家游艇取代了豪车,成为全家追求的目标。 澳洲人生活中最有仪式感的活动,譬如生日、求婚,往往都选在私家游艇上。游艇择港口停放,一般的游艇俱乐部供富人家停泊大型游艇,一年的费用约是8~10万澳币。世界上私家游艇保有量最多的城市,即是*金海岸。因此,它又得名「游艇之都」。 范思哲背后,夕阳时间里,云缓慢地挪动,为海面洒下细微的命运。一些金光在沙滩上飞速倒退,白天蓬勃的热量也以这样的速度消逝。我瞥到许多身影,被撒在海边,闪着细碎的光。太阳从游艇与游艇之间露面,它曾出生,如今将要落下。 这里的鸟并不惧人,只在受到惊扰时才本能地飞起。余光照亮海鸟的翅,男孩嬉闹的声响就从那里传来,被海鸟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晚上在酒店中修完图后,发觉楼下的麦当劳早已关门。迫于夜晚与饥饿,我拉上伙伴,按谷歌索骥,找到一公里外的一家7-Eleven便利店,决定去淘购一些吃食。 黑夜极大,吞掉力与唯物主义。路两侧零星有灯户人家,车辆少,阒静得如同海洋深处,散发着温热安全的气息。 我们两手空空,走在四下无人的夜里,仿佛走在空中,不背负任何重量。这样的夜晚使人安心。我从没体验过如此轻松的夜晚。 路灯偶尔拉长身影,在微弱的光里,绿色、红色、*色的灯牌点亮着旷寂。 只有在夜里,澳洲才变得浓郁一些。电气工业的灯光给夜晚平添了缤纷的重量。甚至奔跑、跌倒,脚步也如同棉花糖一样。 便利店是黑夜中的城市之光。我们像灾难片一样,跋涉许久,在里采购可乐、牛乳、薯片、面包和士力架。 同伴的话语声渐渐在我身后减弱,我向前走去,亚热带的淡风一层一层,潮水般缓慢地涌来。我走到MacArthurParade的转盘路口,抬头望向北方,那是一种逼近终极意义的静寂。我看见星群与大地,看见港湾,电话亭,或者不明意义的灯牌,都在写意的天空下,变得更加深邃、明亮。 /*金海岸摩顿岛/ DAY3 第三天·GoldCoastMoretonIsland 早上起得晚,海上世界(SeaWorld)就在范思哲旁边,移步就到。下午,乘船往摩顿岛,接下来两天,都将在岛上的天阁露玛度假村(TangaloomaIslandResort)度过。虽然我一向对自然风光兴趣不大,但摩顿岛于我,确可与悉尼比肩。 直升机机翼旋转时,带起巨大的风与噪音。那是海洋深处上来的风,吹过公寓楼,水边房,酒吧,游乐场,或者乐园里漂浮的气球,像密集的子弹一样,发出穿透万物之后的回响。 城市在我脚下缓慢下沉,海岸线变得具象。直升机穿过内河,群山,海滩,与*金海岸线;离开Mirage机场到皇家松树,南下至邦德大学和罗比那,横跨木星*场,向北经过冲浪者天堂(SurfaceParadise),海洋世界和南斯特的布鲁克岛,复又着陆在Mirage机场。我看到范思哲,在空中,那座「宫殿」倒也没那么夺目了。 余下的时间,我就在SeaWorld中闲逛。问询买水去处,看气球舞蹈。海风不整齐,穿过洋面与海鸟,木质楼梯,食品铺,纪念品,带着它们的气味到达眼前。这里的蓝色不算夺目,不使人想起悲伤,也谈不上明媚。 乘大巴,往码头去。澳洲车上(公共交通工具)严禁饮食,因为糖分会给车子招来虫蚁。 只要车上有甜食,它们来的速度之快,明明不见一处,但不稍会,便闻味而至。 同时,在车上不系好安全带,一旦被查到,也会被处以数额不菲的罚款。从此处到码头还有些距离,车内的空调开的十分足,不管南北半球,大家对凉爽的追求倒都一致。 码头的船驶往MoretonIsland,是周杰伦与昆凌度蜜月的地方。岛上的度假村,TangaloomaIslandResort,游船接送时会把游客的行李先行接走,并放到游客对应的房间门口。因此,从码头一直到酒店,都无需再受行李之累。回程亦如此。这点确实方便。 行李放在此处,会有专人送到酒店房间门口 不在船上,不知道「劈波斩浪」这个动宾短语的来历。时分已逼近日暮,从这个码头到那个码头,太阳转了个头,就要去往地球另一端了。 沿途偶尔见到轮渡、集装箱、烟囱。到中段,目力所及只有一片海,像一个少年的蓝色目光,直望向摩顿岛。夕阳洒在海上,被海洋的柔波缓慢吸收。 我在*昏之时想起了许多事。夜晚要来了。我想到,远在北方的家乡,航向冰原的松枝树挂,该是什么样子;那里的麦田抽穗,棉花结桃,该是什么样子;巷口街尾的油条铺摊,挂在铁钎上的,是早晨的白雾,还是大陆深冬的寒风。这些割裂般的反差令我异常兴奋。 △摄影笔记:左上第一张照片,是从码头登陆之后,回头发现工人们正在交流而拍下的。当时发现左边三个工人的站姿颇为统一,抓了几张。又是*昏时刻,夕阳的光已经能把人脸打亮了。当然,这里用横构图会更饱满,但相比来说可能会少些层次感。 一直到船停泊在码头,我仍没想到什么具象的画面。太阳已完全下沉,弯月正用肉眼可见的速度攀上中天。 苍穹绛碧,四野有种难明状的韵律,灯光降落,并在岸潮里晃动。夜晚落到每个人的身上,带着黛紫与绀青色,让曾被海洋吸收的温暖再度返回天空,到很低很低的地方,全部的光都涌到天海相接的缝隙里。而不远处,浪正一层一层,像沾了颜料的膏,从大洋深处漫上来。 往后的几个夜晚,弦月沉沉地走步。凉意透过蟋蟀翅足穿抵大地。地平线随潮汐涨落,偶尔听到穹庐内舞灯震聩鼓膜。昨夜的派对更为动人。我时常想起那天,离岸较早,大副的缆绳不着一字,用甲板的方向驶往深夏。 /摩顿岛/ DAY4 第四天·MoretonIsland △摄影笔记:这张题图是从废片篓里救出来的,仅此一张。有时候筛片还是要多筛几遍的好。 行程过半,这天不需赶路,最为悠闲。亚热带的风在早晚吹来,拂过树、火光、银月与星河。酒店离沙滩很近,几步脚程。 我起得很早,但天明得还要早些。这里的房屋建筑都是浅色调,夹映在椰树草林间,不高,低矮,但远看去,一样的干净整洁,精致得像白瓷娃娃。不时从围栏里走出几个妇人,大声谈笑着离去。 我踏过草旁的砖地,棕褐色长砖铺得很远很远,赤足踩上去微微发烫。天气很好。沙滩上的浪已开始前进,每次都冲刷一些细沙。云大块大块地朝海那边挪去,消散又聚拢,搅出细微的痕迹,最终挣脱成风的形状,弥散太空。这一会儿,有些人就很快地变老了。 看云的日子里,时间总过得很快。 岛上娱乐项目很多,浮潜、深潜、直升机、滑翔伞等等,但我并没太多兴趣。大多数时候,我都在岛上闲逛。度假村背后是一座沙山。我和朋友取道草间,顺着前人的路爬上去。太阳已很高了,出来的人多了些,风总不淡不浓。 我眯起眼睛,正一步一步踩进沙丘。由于沙地的原因,上坡时脚吃不上劲,太累。眼皮猩红色的阴影不时盖过来,使人晕眩。 阳光把沙子烙得生烟,没了树荫、海潮,这些细沙和着热量,都跟着脚步往鞋里灌。我下山后,抖一抖脚,倒出了半斤沙子。 站在沙山上,回头看看,海边游人星散,有些微移动,也不及偶尔吹来的风凉爽。那些黑影,遥远得像海边的一颗颗礁石。 沙山上有沙滩摩托的项目,车队排成行,驶成「8」字来回穿梭。当然,沙滩摩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驶执照才可以亲自驾驶,不然只能乘坐。 从高处看去,大海茫茫,可以更好地注意天空。偶尔一株树突入眼帘,它盘虬交错生长的样子显得尤为不同。身后的脚印离散又交错,一个、一个,踩在平静的沙面上,向远处伸去。 △摄影笔记:左上第一张照片,百微拍摄。海鸟和人都很小,但画面各个部分都有东西。 近傍晚时,上船,去看日落。名为「日落巡游」,但只是在日落前后,乘着船进海逛一圈。船上有雪碧、香槟、红酒、饼干等点心饮料供应。 去时天还大亮,近岸时暮色已苍茫了。近日落时,*白色的云在半空中碎成一点一点,又慢慢退后,迎着即将上升的昏光,和太阳一起沉落。等夕阳为万物染上颜色时,那种温驯而温暖的沉默,覆盖了每一个人。我开始看云,但仍无法直视太阳。 海平面处的云有了形状,堆成山形,仿佛为了让太阳落下。它就那么一点一点往下掉。掉进云里,掉进海里。等到它全没入海面后,只留下一点昏光,而月亮已很高很高了。在安静处,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黑暗正一点一点漫上来。 入夜,码头处的喇叭不断循环宣读着喂养海豚的相关事项。这里的野生海豚有九只,每晚七点时,来到此处的海滩觅食。游客们排好队,由工作人员牵引,消*,把着手,将鱼喂给海豚。 海豚的眼睛十分脆弱,一般的闪光灯会对它们的眼睛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因此喂养海豚时是禁止游客拍照的。不过有专门的人员为游客们拍照,他们使用特制的闪光灯,从海豚背面拍摄,一人兼顾两条喂海豚的海豚路线,跑来跑去。 黑夜来时,岛上可以听到蟋蟀的声音。星斗旋转,一点一点洒进海面。海上的波光像一幕电影镜头,伴着灯塔的光迈入旷寂,只有厚重深邃的黑暗在远处高蹈不停。这边的灯火渐渐稀疏、零落,海的那头,世界正阒然入眠。 /摩顿岛悉尼/ DAY5 第四天·MoretonIslandSydney 上午离岛前,度假村的Café中可以听到一些歌舞声。这时就知道,南半球的圣诞前奏已经来了。 在澳大利亚,有着与北半球迥异的圣诞节。人们盛装出行,但一副清凉模样。每年都有许多欧洲、北美的游客,来到澳洲,在盛夏炎炎的时候,过一次「红色圣诞节」。 那天依然很热,只是没有蝉鸣。沙山上高枝晃动,层层腾高,阵阵远去,白色的大鸟飞过密林,渡过河,到山的背面去了。我们依旧乘着来时的船,走来时路,倒退回悉尼机场。 抵达悉尼的索菲特酒店(SofitelSydneyDarlingHarbour)时,天已全黑下来。墨色浓重,从酒店窗内望去,山雨欲来。阴云不言语地积聚,远景逐渐不可分辨。云层间撞出几道落雷,紧接着,大雨就飘到了这边。为了拍摄,屋内没有开灯。雨势骤大,我坐在地毯上,望着颓然的雨雾,像望着许多年前被大雨困在家中的自己,一样地昏暗,茫然。 这场突来的大雨十分夏天,滚雷阵阵,积雨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移去,预示着不久大雨将停。酒店脚下的路交错,雨声越来越密集,连成线,密不透风的网一样,扑向偶尔出现的行人。雨幕将行人遮蔽,显得愈发不真实。接着,撑伞的那人便消失在黑暗里,仿佛未曾走过这一遭。大雨隔绝掉人与城市之间的熟悉感。打开UberEats(在澳洲点外卖可以用UberEats,店家多,质量好。不过在AppStore上中国区的账号无法下载此App),店家几乎全歇业了。 澳洲的生活开销对国人来说十分昂贵,任何金钱的耗费都需要乘五计数。一顿外卖,在澳洲与国内虽然都是三十元,但由于币种不同,国人需要支付五倍于此数值的RMB。所以,既然来到澳洲,日常生活最好不要将澳元换算成国内货币,不然面对一瓶动辄十几元的矿泉水,很可能连饭也不敢吃了。 一次短途打车与两次外卖的账单 索菲特酒店一样配有专门的中文服务员,如果恰巧前台没有中文服务员当值,可以向其他人要求找一位过来,因此,在酒店内基本不存在交流上的困难。酒店房价大约为澳币(约合人民币元)每晚,但由于其绝佳的地理位置(情人港旁边)与特别舒适的入住体验(床品舒适程度不亚于范思哲),依旧物有所值。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酒店内严禁吸烟(澳洲所有室内场所均严格禁烟,必须在看得到天空的户外才可以吸烟),一旦被逮到(几率极大),一个房间罚款澳币(约合人民币0元)。另外,酒店的地毯也不允许泼洒上饮料等难以清理的污渍,否则均需照价赔偿。 骤雨一过,云就散去。远远地飞机的航灯明灭,飞过海港大桥,到我身后去,一架接一架地,在夜晚清澈高远的奏鸣曲中飞过。 /悉尼/ DAY6 第六天·Sydney 悉尼今天是清爽的。一早起来去海鲜市场,又去到塔龙加动物园,DFS免税店;下午往情人港,坐游轮环港。 但大部分时间,我的精力都不在这些具体的游玩项目上。我始终注意着远处,那些沉浸在光亮中的钢筋水泥,或是拘窄小隅。这些目光的转移,让我开始沉入这座城市,慢慢地用目光抚摸每一幢建筑。 哈林顿街上有一处免税店,即DutyFreeShop。在市区DFS中买到的商品均可以享受免税价格,但所有商品都会被密封,必须出境后才可以打开。澳洲的GUCCI与其他地方比起来非常便宜,但一次不要买太多。 商品会与护照绑定,在信用卡中先行按照免税价格划扣。需要拿好购物时给的单子,在机场申报退税。澳大利亚的进口税率是10%,去掉手续费后,大概能退回来9%。但是,市区DFS买的化妆品、红酒之类的液体必须放到行李箱里托运。 机场免税店及市区DFS 此外,机场的免税店不时会有打折活动,这次是满澳币以上,商品可享受95折。因此,考虑到折扣与携带的因素,我没在DFS内买任何东西,一律留到了两天后的机场免税店解决。实际情况,还要结合当时的折扣情况以及要买的物品决定。 只在DFS中逛了一会儿,我就出来,到哈林顿街上。这似乎是很有历史的一片街区。 右图是一家已经停业的*屋 从拐角处的酒馆走出两三个人,他们走向电话亭、指示牌与路灯。我往里面探去,光线昏暗,古铜质地的高脚椅围着圆桌,人们都在更暗的位置坐着。 坐在这家EndeavourTapRooms中,找不见光的角落,和朋友喝上一杯精酿,智美红帽,角头鲨也可,看看外面阳光灿烂,人流过往,这将是十分文学的一个下午了。 也许屠格涅夫、左拉、莫泊桑、福楼拜会围坐在中间块小圆桌上,一杯一杯地,喝下一些浪漫主义的味道。我会推荐福楼拜老师尝一尝罗斯福10号,那种十足淳厚、宽容的口感,很适合他。屠格涅夫在大醉后一把拽住左拉,说:「用不着把我的悲痛告诉你,他是我最爱的人。」 澳洲龙虾、牛肉都很出名。海鲜市场中的澳龙个头极大,据说干净到可以直接生吃。但价格很贵,随便买一些也要上千元。 海鲜市场外面是一处小港湾。许多海鸟我叫不出名字。但它们随意飞来,停在有人的桌上,对人类完全不作戒备。放在国内也算是「西洋景」。 此处很多华人面孔,连售货员都是亚裔。澳洲人闲散,周末绝不加班。所有工作外的时间都可以拿来享受。 他们对财富的追求好像没有那么急切,有个目标,生活的奔头够那个劲儿,就行。所以,周末还上班的,大多数是亚裔面孔。 塔隆加动物园的历史我没心多听,动物亦不感兴趣。进园区,有一个免费缆车,可以横穿动物园,直接到动物园另一头。那边可以远望悉尼城。 我二话没说,进了园子直接坐上缆车到另一头。下了缆车往下走,到小港口,隔着海湾,可以看到悉尼歌剧院,达令角(DarlingPoint)、派珀角(PointPiper)。 从悉尼城中看悉尼。仅仅是买了票,来到这里看一会悉尼城,也是值得的。 为了这种值得,我在这里站了一个多小时,看着形状各异的大小游轮,驶来航去。不过,这里的小卖店并不支持信用卡,只可现金支付。对于那些没能看到的动物,我倒没什么遗憾的。 情人港,也叫达令港,只是意译与音译之分。各样的圣诞树已摆了起来,也有人打扮成圣诞的样子,走来走去。游轮不停离岸、靠港。我们只是要坐游轮绕港一圈。 等船的时间很久。我在港前走来走去,看许多神似的人上船下船。来的都是游客,但国内游客最喜欢成群结队,也难怪,大部分是夕阳游老年团,因此在船上,丝巾是少不了的,自拍杆是少不了的,保温杯也是少不了的。 天渐渐阴下来了,越是近港,风越是大。 上了船就可以开始用餐。游船上有三道式晚餐。蔬菜沙拉,主餐是鱼,甜点是小蛋糕。虽说都是新鲜烹制,但指望它们填饱肚子不太可能。我对饮食尝味没什么天赋,不懂得精细地分辨它们的好坏。但有一事可以确定,晚上又要外卖加餐了。 天完全阴了下来。我已经无意用文字去粉饰当时的景色了。甲板上风极大,从悉尼的每个角落吹来。我站在风里,扶住要被吹走的渔夫帽,不知自己在想些什么。 /悉尼/ DAY7 第七天·Sydney 多年前,我在《看不见的城市》里读到,「记忆既不是短暂易散的云雾,也不是干爽的透明,而是烧焦的生灵在城市表面结成的痂,是浸透了不再流动的生命液体的海绵,是过去、现在与未来混合而成的果酱,把运动中的存在给钙化封存起来:这才是你在旅行终点的发现。」 城市在我离开后,就不再是具象的画面,而变成了一些时间节点的记忆。我只能靠直觉去捡拾它们。 第七天是我自由活动的一天。但城内仍不时下起雨,多少有些不便。 前一天,导游提出要带我们游悉尼歌剧院,但收费甚高。于是我当即在马蜂窝上预定了悉尼歌剧院的中文讲解。 讲解分为30分钟和60分钟档,60分钟档为人民币每人,包含门票与中文讲解。可以进到演出用的内厅中参观,只是像歌剧厅之类的某些地方严禁拍照。参观时,双肩包必须寄存,单肩包则不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第二天的讲解预约必须在前一天下午4点前进行预定。 悉尼歌剧院共有三栋建筑,最高的为主建筑,后面的一栋为歌剧厅,另一栋则是餐厅。建筑的整体高度与皇家植物园的高度相同。导游是台湾人,讲解也谈得上生趣,不致使人昏昏欲睡。 这里是悉尼艺术文化的殿堂,是悉尼的灵*。 为了使更多的自然光进入室内,西部走廊的大窗户,呈外小里大的向外伸出的形态。也正是基于多用自然采光的理念,建筑物里面很少看到辉煌明亮的大灯。 剧院内有两个大剧场,三个小剧场。小表演厅可以容纳人,因为舞台小,为了便于拆掉扩建舞台,所以前三排的位置是平放的,而非阶梯状放置。 外部的玻璃呈45°角伸出,是以防止室内远眺时玻璃反光故。这些玻璃当时均是法国制造,远渡重洋来到悉尼。 悉尼歌剧院的玄妙与历史很多,我无法一一记叙,而这些在长久的岁月后也终将淡远,交给维基或者百度。 我只是记得,上到二楼,抬头,可以在头顶的玻璃上看到倒映的海港大桥;悉尼歌剧院的外壳并非洁白如玉,而是盖着一层蛋*色;歌剧厅内说话不用麦克风,整个厅都听得清晰无遗;内部结构秩序而繁复,展示着人类辉煌伟大的智慧,和那半世纪来艺术与思想的灵光。 悉尼歌剧院二楼,头顶的玻璃可以倒映出海港大桥 离开悉尼歌剧院时,雨势极大,且来得极快,热烈地像管风琴的演奏。这里雨势急促猛烈,很快连成一片喧哗。像北方城市里,深夏午后突如其来的暴雨。 沿着长廊,我走了很久很久。人们在雨中自己做着自己的事情,全然轻松,而圣诞的气息已渗进这座城市的各个地方。不管看了多少次,对于盛夏里的圣诞,我仍然有足够的好奇。 前一晚,索菲特酒店,有人将一封信塞到了每位房客的门缝里。信中大意是说,这天下午5点,圣诞老人会用绳索从酒店的35楼滑到1楼,5点15分时在酒店大堂举行圣诞歌颂表演。也许缘分未到,五点时,我正在街上奔波,没能赶回酒店。不过仅是收到这封信,这样的浪漫,已足够慰藉了。 我在雨中奔去临近的地铁站,这里的地铁单程票是纸质,并不回收,可带回家权当纪念。它更像一个小型火车站,老旧且充满电影感,连列车都是软座,乘坐舒适度比国内好上不少。 薄雨稍住,傍晚时分,我走到PittSt.上,听到有人在用小提琴演奏《Clock》。我还是第一次在街头看到有小提琴表演。 B-BOX、LOOP再加小提琴演奏,伴以点弦,他一个人把歌曲的层次打造得丰富无比。在国内,不可想象能遇到这样的街头表演。我在那里站了一个小时,向琴箱里投了30澳币,带回了一张他的专辑。 后来,我在Instagram上找到他,CamNicholson,这是他的名字。他似乎全球周游着在街头表演,不久前,刚从英国回来。他喜爱摩托,自幼接受钢琴、吉他、小提琴的音乐教育。在他那里,我窥到了另一种青年的人生。 悉尼城市的气质,在阴雨里,我无法一一领略。它闲逸清朗,有着与成都相仿的温和,但从里到外的干净质朴,像大巧若拙的璞玉。 比喻是使事物失真的方式,但于我而言,只有比喻才能完成从一种失真到另一种失真的架构。 关于悉尼,它存在于塔隆加动物园港湾处飞过的海鸥身上,在海港大桥飘摇的澳大利亚国旗上,在深夏盛大无声的暴雨里变成一滩又一滩想象。 异国异域中,道路轻轻曼曼,横斜直曲,环顾也还悠然。 这些古朴、现代、典雅,混合在一起,高接层云,再以圣诞节为佐料点缀,走在悉尼街头都是自由,是灵光,是无处不在的新意与夜晚深处滑落的芒星。 /悉尼/ DAY8 第八天·Sydney 今日简单,简单到足可一笔带过。往悉尼塔旋转自助餐厅、悉尼大学,便到返程时了。 没有什么比一个旋转的高塔更适合观看城市全景地方了。餐厅的自助种类相当丰富,尽可大快朵颐。 阳光之大,在一个短暂的雨天后又露了出来。 我回国后与朋友聊天,把日本和澳洲放在一起,再反观国内,纷纷自惭形秽于身处何等粗糙的国度。集体主义与宏大叙事,让我们这个民族不擅细微之情。于是,街角亭堍都是大起大落,大开大阖,艺术虽广大已极,但在这样的大开大阖面前,连艺术也缩微成鸿毛了。并不知我们有多少吉光片羽可留给后辈。 他说,之于日本的印象,是在高速公路上望见海,与五色的天。天空淡粉盈盈,接目而来是蒸汽时代动漫里的工业区,大片大片地,如同一个节制又洪流暗涌的钢铁巨兽。 京都街头,所谓的唐风宋韵,我曾一遍遍在舒国治笔下领受过: “太多的风流蕴藉之事,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你皆可扮上一个动作,披上一片布幔,挥动一件道具,而数百年来中国早已失落的雅观风致,或在你的履践中,不自禁地消受了。” 日本人精致的背后是压抑:精神性的压抑。因此也催生出许多矛盾摇曳的艺术。但澳洲人不一样,他们全然轻松,物质富裕。若说日本是东方式的精致,澳洲就是西方式精致的翘首。 在旋转餐厅上望着林立的楼倒退,它们好像一个总结,在我将离去时把悉尼摊开在我面前。 我该认得曾去过的港湾,涉足过的广场、街道,从楼宇夹道中抽离后,我都能看到它们——但我认不出来。 我冒雨去过的ChemistryWarehouse,Woolworths,它们都被连绵延伸的群楼淹没,在一场灭顶的阳光里飞速地淡褪、同一,变成旋转都市里的一个个质点。 赶去悉尼大学时,离赴机场的时间已很近了。大多数人只是在门外转转,与这个哈利·波特的取景地合影。 我钻进门里面,企图用少得可怜的时间看一看这所澳洲第一校。它美得不像一所大学。我无法描述这些建筑,只能用图片传达。 这里的草坪、青年、方尖顶,倥偬百年,总让我想起木心在《哥伦比亚的倒影》中提到的一景: 草坪上的年轻人比石阶上的更多,男的近乎全裸,女的已是半裎,大意是享受初夏之日光,三五成群,轻轻谈论,时而婉然卧倒,就此不再起来似的。 第八天,我已基本适应了英语环境,并因能有机会与人交流而兴奋,哪怕只是求取道路,我也乐得与他重复确认几遍。 离开前,我看到一个摄影师趴在地上,为一对新人拍摄婚纱照。此时烈日直射,新人背后一片枯瘦杂芜,我因此对他的业务能力产生了一些怀疑。不过也因此知道,全世界摄影师为了出片,都无所不用其极。 这是我身在澳洲时拍下的最后一张照片。 往后,过关,出境,无尽的航行,宇宙与星群,赤道之浩莽,晨昏线消失,都在飞机上的一张毛毯里。过了长夜,便到成都了。 我在一个缭雾初散的清晨,走向家,怀揣遥远大洋的湿气,此时阳光必得透过树丛,小街也明暗,不知几时阵雨便沛然而下。有些蓝色,长长的,一下掠过耳边,带起一阵爽利的哨声,在一个金发青年的琴弓上跳开,远不如梦,且不似戏。 我自此长久地想念起那些渺然的微风了。 -End- 策划/亦池 摄影/亦池 文案/亦池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亦池手可摘金币。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ozhoulongxiaa.com/azlxjz/8911.html
- 上一篇文章: 艳遇行膳姹紫嫣红四月天,我和美丽有约
- 下一篇文章: 精品创新菜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