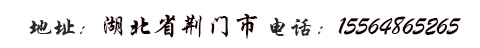梁昭ldquo谋杀母语rdquo
|
哪家治疗白癜风权威 http://pf.39.net/bdfyy/bdfyc/150505/4618897.html医院订阅哦! 梁昭,广西柳州人,现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同时兼任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副秘书长、四川大学《文化遗产研究》(辑刊)副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人类学、中国多民族文学、比较文学。 第一位获得“威尔士民族诗人”称号的格温妮丝?刘易斯(GwynethLewis,-),是一位使用威尔士语和英语双语创作、探讨母语与认同主题的当代诗人。她创作的以“谋杀母语”为主题隐喻的一组诗,采取对话、幽默、嘲讽等语调,表达了文化认同的艰难与复杂。此外,诗人所作的双语诗歌镌刻于威尔士的首府卡迪夫的地标性建筑——“威尔士千禧年中心”外墙,鲜明地表达了双语文化共存的愿望。刘易斯的创作实践揭示了威尔士几百年来并存的双语文化现实,对在当代多元文化的语境下创造性地继承本民族文化,富有启发意义。 民族语言历来是民族共同体的重要表征。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更被世界当代多个国家视为维护少数民族权益的标志。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跨国组织开始以公约、宣言的形式提倡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把少数民族的语言能否延续与少数民族能否存续的联系起来。在这种背景下,少数民族作家越来越多地在作品中表达出对母语问题的关切,同时在全球交流的环境中承担起对外交流的任务。 本文讨论的焦点是英国的一位当代威尔士诗人——格温妮丝?刘易斯(GwynethLewis,-)——的英语写作实践。这位诗人是当代威尔士一位具有象征意味的民族文化代表,她坚持双语(威尔士语、英语)创作,在诗作中突出地表达了“谋杀母语”的主题,在双语文化环境里塑造了双语表征的文化景观……对在当代多元文化的语境下创造性地继承本民族文化,富有启发意义。 格温妮丝?刘易斯(GwynethLewis,-)一格温妮丝?刘易斯(以下简称为刘易斯),当代第一位荣获“威尔士民族诗人”(NationalPoetofWales)称号(年)的双语诗人。她出生于英国威尔士公国的首府卡迪夫,从小学习威尔士语和英语。自年代起开始用威尔士语创作诗歌以来,她凭借威尔士语诗集荣获两次威尔士尤尔得全国年会(UrddNationalEisteddfod)的文学奖章。其英文作品如下: 诗集: 《寓言与传真》(ParablesFaxes,),获得英国奥尔德堡诗歌节奖(AldeburghPoetryFestivalPrize) 《零重力》(ZeroGravity,) 《保持沉默》(KeepingMum,)获得威尔士艺术协会年度书籍奖提名 《混乱的天使:英语诗集》(ChaoticAngels:PoemsinEnglish,) 《麻雀树》(SparrowTree,) 长诗: 《医院奥德赛》(AHospitalOdyssey,) 威尔士民间故事改编: 《肉树:马比诺吉昂的新故事》(TheMeatTree:NewStoriesfromtheMabinogion,) 剧作: 《克莱登妮丝特拉》(Clytemnestra,) 自传: 《雨中的阳光浴》(SunbathingintheRain:ACheerfulBookonDepression,)、 《双人同舟:一段婚姻的旅程》(TwoInaBoat:AMaritalVoyage,)。 总的来看,刘易斯的作品多以威尔士文化为主题:威尔士的历史、威尔士的民间传统、诗人对威尔士的情感等等。除此以外,她还重写威尔士的民间故事,把莎士比亚的剧作改编成威尔士语上演。 与英国很多拥有威尔士民族血缘的作家一样,刘易斯对于威尔士文化认同问题尤为关切。她的两本英文诗集《寓言与传真》、《保持沉默》,收录了很多关于这一主题的诗歌。这一主题的诗又突出而具体地以母语和母语文化的消亡为中心内容,把这一内容置于“母语和母语文化的消亡——人的追寻/侦察”的书写模式中加以表达。在刘易斯的第一本英文诗集《寓言与传真》里,《寻找凯尔特人》、《威尔士间谍》等诗,都运用了大量死者、坟墓、老树、碎骨等词语和形象,来比喻威尔士文化的逝去。同时,面对衰老而正在消逝的文化,诗人创造了该文化族群后裔的形象,让他们去“追寻”文化的遗迹,“侦察”文化的现状,寻求某种可能的答案。这意味着诗人为威尔士文化赋予了某种神秘性,又许诺了这种神秘性将得到揭示。 在这一时期,诗人对文化消逝表达了缅怀、伤痛的心情,对消亡背后的神秘原因作出了阐释。如《威尔士间谍》组诗的最后一首: 他像他的语言一样衰老。他的双手布满皱纹 像风吹弯的树木,放在瘦骨嶙峋的膝上 那树曾经很挺拔,当他年轻时。如今他老眼昏花, 满溢着眼水。如果你和他说话 他提到的人你一无所知, 他们都已进了坟墓。他也不知 你是谁,你如此尽责地造访塔里宝特 是为了什么。 这就是语言何以死去——言语 忘记了它所熟知的,年轻人 不理解权利所要求他们去做的。 最后,精英们一去不复返,永远地。 在这里,今昔对比、老人和年轻人的对比很清晰地传达了文化衰老和消亡的主题;而这种把自然时间的流逝作为喻体的写法,强调了文化消逝的“自然性”以及人的无可奈何。此处的“神秘性”,被归结于有限的人面对无限的时间所产生的茫然无措感。这是很多关怀弱势文化的作品显示出来的普遍主题。 以消亡-追寻/侦探的基本模式,来表现文化之神秘和人的情感反映,在刘易斯年以后出版的诗歌中保留了下来,但有了精妙的变形——变成了“谋杀-侦探”的模式。诗集《保持沉默》的第一部分,题为“语言谋杀者”。第一首诗《一个诗人的自白》写道: “是我做的。我杀死了我的母语。 我不该让她 独自留下。 我想要的是一些快乐 用另一具身体 但现在她已逝去—— 可怕的沉默。 她曾经高度敏感, 很有可能心怀忌妒。 毕竟,我正年轻, 而她,曾经的美人 变成了一个老妪 即使经过手术治疗。 我能挽救她吗? 能让她感觉自在吗? 没有了她的责备。 我感到如此麻木, 并不自由,不像我曾经想的那样…… 叫我的律师来。 在他到场之前, 我将保持沉默。” 刘易斯诗集《保持沉默》诗人把语言的“消逝/消亡”转变为“被谋杀”,这就把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转化为另外一种具有突变性的、具有阴谋论味道的事件,向读者渲染了一种更大的神秘性,同时还有震惊。因为这首诗的开篇明明白白交待“我杀死了我的母语”,整首诗因此犹如一个凶手的自白。然而自白并非对行动有条理的说明,而是情绪的宣泄——表达了茫然不知所措的怀疑:“我感到如此麻木,并不自由,不像我曾经想的那样……”在阅读求解的过程中,读者不再被引向对感伤情绪的共鸣,而是被邀请去思考行动主体的选择。 诗集中的其他诗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母语”与“我”的联系:《母语》以黑色幽默的语调,写一个“语言迷恋者”需要一个“多语种的男人”,而让威尔士语“活下去”的途径,是“只要我使自己/保持得更纯粹,拥有更简单的品味”;《她的结局》描绘了令人震惊的画面:把母语比喻为人临终前从体内滔滔流出的鲜血;《失语症》用哀婉的调子说:“有人剪断了线/在每一个词语及其所指的事物之间”;《头脑风暴》询问:“追寻谋杀者会怎样?这会使我变得疯狂/还是让我成为一个诗人?”…… 这些不同语调、不同角度的诗篇,展示了“母语”在当代的尴尬处境。同时,诗不断引入鲜血的意象、性的关系、家庭关系,来暗示“母语”之于身份认同的密切联系;更大量将威尔士语直接植入英文诗行中,达到评论家所说的“使得少数状况(minorstatus)变得可见”的效果。如《她的结局》 ……从她的嘴里 冒出词语的激流,daywdant iataltafod,gogoniannau’rTad 在鲜红的花丛中——ynAbercuawg ydganantgogau——血是黑色的, 满是污秽,尤其令人惊奇的是 那些生动的成语——bola’nholiblemae‘ngheg?—— 总是很丰富,yesnopwdinllo 赞美诗正聚集在她的体内 喷涌而出…… 最后,诗人用“谋杀-侦探”的模式,创造了一种惊悚而令人震惊的氛围,提出了悬念,但她没有再援引熟悉的模式——生命的自然死亡——作为解释的可能;而只是用不同的诗篇探索谋杀者与被谋杀者之间的关系,将两者之间的复杂情势一一揭示出来。谋杀的原因——神秘的阴谋——得不到解答,这刺激着人们继续去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ozhoulongxiaa.com/azlxsh/9970.html
- 上一篇文章: 年高考35月各地模考语言文字综合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